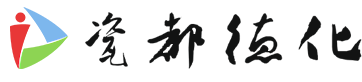外婆的灶台,是典型的闽南灶,在厨房的墙角处,“一”字排开三个灶眼,最大的安在中间,一口黑底大锅横卧其上,那是外婆张罗一家近十口人伙食的家伙;右边的灶眼,临着一口水缸,安着小锅,平日里炖汤或煮些清汤面线;左边的灶眼,依着墙根,常年烂炖着糠菜,那是竹林里漫野飞奔的鸡鸭,以及柿子树下被圈养的猪的口粮。
年幼的我,最喜欢跟着外婆,围在灶台边上玩耍。帮外婆挑菜,抓青菜虫吓唬小表姐;抱着柴枝,往灶膛送柴火,看灶火噼噼啪啪地烧,松油在外头汩汩冒泡,再用小树枝将它们挑破;把脸往灶前靠,让灶火把小脸烤得滚烫;忙着抓起灶台上的空竹筒,对着灶口一阵乱吹,享受竹筒响起的“呜呜”声;对着熏烟闭眼憋气,让眼泪哗啦啦往下掉;在一堆柴火中寻觅小铁铲,一铲铲地铲出灶底的灰,学大人模样,将它们洒覆在因为漏雨而湿洼的地上……
有时候,外婆看着我,会哈哈大笑,那是因为我把空竹筒弄错边,黑灰堵了一嘴;有时候,外婆也会微微蹙眉,因为我把灶灰扬得到处都是,一大锅来不及盖住锅盖的饭菜,免不了多添些“调料”;有时候,外婆会用松枝打我的小手心,因为我离灶口太近,灶口的灰都跑到衣服上……
外婆的灶台上,到底煮过怎样的美食?时光长久,我竟丢失了许多印象。只记得有一次,外婆蒸了一大锅的馒头,揭开锅盖那一刻,雾气弥漫了整间厨房,馒头的香味随着雾气迎面扑来。朦胧之中,舅舅们把馒头切成棱形的一块块,外婆挑了一块,在手上翻来翻去,吹了又吹,递到我手上。热乎的馒头,暖着嘴上,融到胃里,甜在心底,成为我小时候最回味的味道。
后来,父母带着我入城求学。每次寒暑假,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外婆家,因为在那儿,我不仅可以肆意在田野里摘外婆种的瓜果,小溪里捉鱼虾,竹林里抓昆虫,乡间路上滚铁环,还可以陪着外婆在灶台边兜兜转转,往“灶脚”埋几块番薯、芋头;偷偷掀起小锅,挂几只昆虫在灶眼上烤出一股焦味,再撒上几颗盐;在水缸上的案板切几段黄瓜放碗里,搅拌些许白糖,吮吸着瓜中渗出的甘甜汁水……
蹲坐在灶台前,帮着外婆烧火,是每次回家的必修课。当我拗着松枝往灶膛里送,外婆“哒哒哒”打着蛋,火候一到,便将蛋往大锅里倒,“兹”的一声响,鸡蛋的清香,弥漫开来。而后,放入香菇和瘦肉,稍稍搅拌,倒入盐,加上清水,等水开了再放上些许的米粉,点缀上葱花或青菜,不一会,一碗金黄的鸡蛋瘦肉香菇粉汤,便摆到我的面前。
最吸引我的,不是汤粉中白白胖胖的粉条,不是金黄金黄的鸡蛋,不是翡翠如玉的葱花,而是每次夹在其中的零星草木灰,一点一点黑乎乎的,也不知是锅里炒焦的,还是灶台扬起的,抑或是屋顶脱落下来的。
我捻起筷子,捧起碗,小心地吹几口气,抿上一口,滚烫的汤汁,融着瘦肉的甜,香菇的滑爽以及鸡蛋的清香,不腻不淡中又夹杂着些许草木灰的苦,成了我求学岁月中难忘的味。
我慢慢长大、成家。外婆也慢慢地从灶前的忙碌,挪到灶边的安坐。
那一天,夕阳的余晖照在她鬓霜的白发,隐隐发着光,照得她眯起的双眼,和刻上岁月痕迹的皱纹挤在了一起。我走上前,轻轻呼唤着她。外婆在阳光的细缝中努力睁着眼,上下仔细打量我,眼中泛起喜悦的光,她婆娑的双手紧紧拉住我,喃喃叫唤我的名字。
只是,那个名字,从她的口中飘出,在空中却被风给吹乱,最后传到了我的耳朵,变成了弟弟的小名。
我的悲伤,像灶台上被忘却的滚水,奔涌而出。